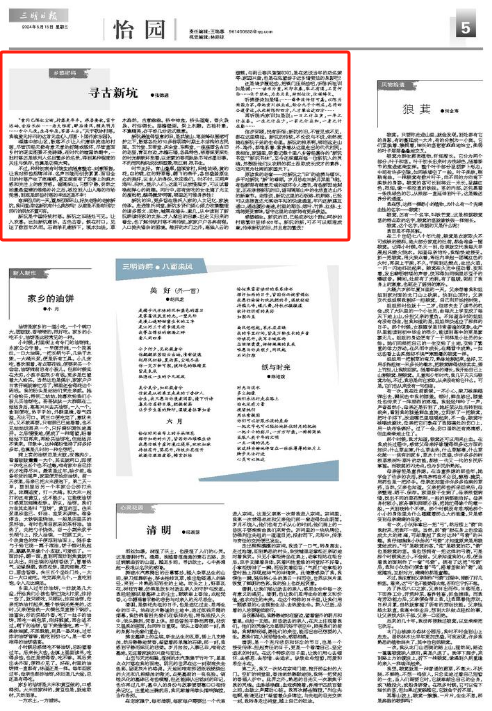
“重冈已隔红尘断,村落更年丰。移居要就,窗中远岫,舍后长松 ……老夫惟有,醉后清风,醒来明月……古今几度,生存华屋,零落山丘。”关于歌咏村落,我偏爱元好问的这首元曲《人月圆·卜居外家东园》。
福建中部山区,散落不少让人们意欲流连的村落,尽管历经无数有意无意的折腾或毁坏,尽管直面乡村的现实图景不免踌躇,在时代的喧嚣热潮中,一批村落还是被列入名目繁多的名录,得到某种程度的关注与保存,也算是功莫大焉。
不过,种种初衷有时演变成随意整容、刻意贩售,让我对那些招牌洋洋、名声日隆而创伤累累、面目全非的村落产生了疼痛感,甚至渐渐有了伤害上的麻木感和关注上的疲劳感。偏隅深山,习惯宁静,突然之间遭遇蛮横的修修补补之后,被拉到人山人海的市场兜售,到底是那些村落的幸运还是不幸?
春深四月的一天,置身四面环山,好友老陈的老家新坑,我问道:取名新坑有什么典故吗?从前是不是有旧坑?同行的朋友不置可否。
新坑是中国传统村落。新坑之旧随处可见,让人欢喜。比如新坑廊桥,古色古香,候在村口,见证了数百年风雨。石砌单孔廊桥下,溪水如线,草木森然,古意幽幽。桥中神龛,桥头道庵,香火袅袅,村俗绵长。屋檐壁画,梁上木雕,古拙朴素,不算精美,亦平添几分老式雅意。
新坑最值得留意的旧,是武陵山、笔架峰似围裙呵护之下,散落各处的50多栋明清时期土木结构的古民居。玉竹堂、玉带堂、庆余堂、东熙堂,一座座厝名古旧的老屋,青瓦白边,木檐石墙,各具特色,被春深更深处的时光款款环抱着,以迷蒙的春雨脉脉书写水墨旧事,不约而同构织成农耕图景,很江南、很书生。
时节正好。青山叠翠,碧溪穿村,田畦浓绿,黄的花,白的蝶,红的野草莓,翻飞的燕子,各自盛装原生态的美好,以主人的身份,欢迎我们。时不时,三两声鸡叫、狗吠,提示人们:这里可以放慢脚步,可以试着唤起禅心的闲趣。同行中,却有贪吃的女生摘了无主的瘦枇杷,酸得龇牙咧嘴,哪里还可修身养性?
新坑的旧,更多留在陈氏人家的人文记忆、家族传承。走进陈氏祠堂,新坑乡贤们倾心倾力收集整理的诸多图文、实物,铺展在墙头、案几,从中读到了新坑耕读传家的文脉、才人辈出的自豪、出走又归来的眷念,也了解传统村落不再传统,家家户户各奔前程,人口流失错杂的困境。敞开的木门之外,高耸入云的旗幌,与闲云春风絮絮叨叨,是在述说当年的功名荣辱、家园兴衰,也是在张望游子近乡情更怯的身影吧!
还是请步履轻些,把嗓门压低些吧,听陈氏祖训如是诫:……读书为重,次即农桑,取之有道,工贾何妨……仕于朝也,为忠为良,神则佑汝,汝福绵长。
听溯源诗如是唱:……舜帝流传信可嘉,以陈为姓国为家,择地贡川祖业成,馀公九子十科名,志将四公遗骨迁,从此新陈衍四方,人才辈出达四方……
再听陈氏家训如是说:一日之计在寅,一年之计在春。一生之计在少,一家之计在和,一身之计在勤……
信步环顾,恍有所悟:新坑的旧,不管见或不见,都在这里绵延。新坑的传统,不论说与不说,依然流淌在新坑子弟的生命里。新坑的根系啊,哪怕远走山外、海外,都维系着、营养着从这里走出的代代村民。我相信,家谱里,骄傲记载十里八乡曾经嘉许的“新坑书篮”“新坑书林”,至今还深藏在每一位新坑人的灵魂,并激励他们从农耕的泥土汲取成长成才的素养,迈向更为壮阔的家国天下。
原谅我的老套——对新坑之“旧”的追溯与缅怀,多于对新坑 “新”的眷顾。岁月总在日新月异里飞驰,有些新带有肆意无端的破坏令人遗恨,有些新因地制宜,正在承接新坑的旧,谱写隅居山中的生活直达山外的新章节。老陈说,新坑这里的石板路、机耕路,已经可以连接直达尤溪动车站的快速通道,年内还新建互通口,通连厦沙高速,村里的稻谷、烟叶、竹笋、红菇、土鸡将更受青睐,留守这里的农家将有更多获益。
感慨顿生。新坑的旧,已经庇护这个群山呵护的村落繁衍呈祥600年。新坑的新,可不可以顺理成章,传承新坑的旧,并且愈加繁茂?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