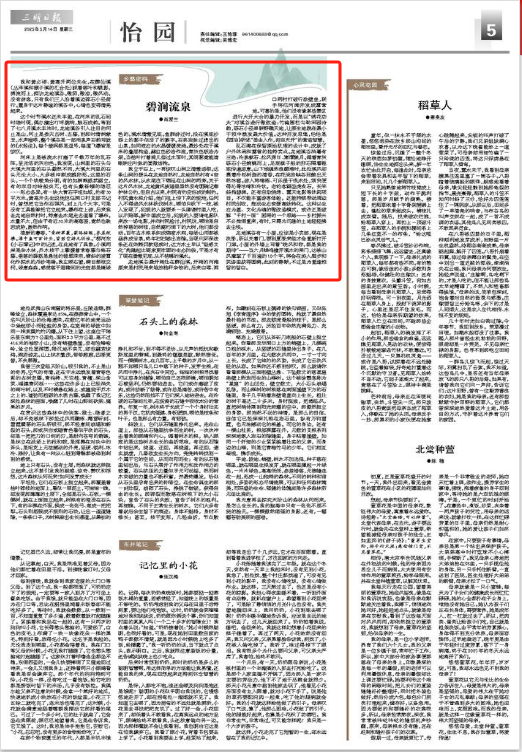
我和黄必祥、黄高升两位先生,在醉仙溪(丛洋溪和猴子溪的汇合处)踩着落叶和蝶影,溯流而上,探访龙地溪谷。微阴,微凉,微风动。没有游客,只有我们三人沿着溪边碎石小径前行。置身于这片静谧的溪谷中,心情也变得清亮起来。
这个时节溪水还未丰盈,在河床的乱石间时隐时现,偶尔撞出叮咚脆响,触石成韵。等到了七八月溪水丰沛时,龙地溪谷引人注目的何止是山,何止是参天古树、古藤,到那时清涧漱玉,水声喧哗,整个溪谷是一部用泉声石韵写就的《水经注》,每个漩涡都是逗号,每道飞瀑皆是惊叹。
河床上是被流水打磨了千载万年的乱石阵,呈光洁的灰白色。我发现,山涧里的石头与大溪大河里的石头截然不同,大溪大河里的石头无论大小,大多被冲刷成鹅卵形。这里的石头,一个个块棱角分明,有的如狮熊威武踞立,有的双目对峙般突兀,也有头戴苔帽的隐忍……形态各异。有一块大青石平坦如坻,约有30平方米。黄高升先生说他担任洞口村支部书记时,曾想把它当作石屏风,刻上几个大字,可是没有工具能够把它立起来。瀑布在上游,后来我去龙地自然村时,特意去水尾走古道看了瀑布。水量不大,但由于有近30米的高落差,竟然也跌宕成势,轰然作响。
清新的暮春,“青树翠蔓,蒙络摇缀,参差披拂。潭中鱼可百许头,皆若空游无所依。”柳河东《小石潭记》中的记述,在此地有了具象。小溪两岸是杂木林,乔木枝干上攀援着常春藤与络石藤,垂落的薜荔是悬挂的翡翠珠帘,横斜的凌霄化作探水的丹砂笔锋。我左顾右望,满目翠枝交柯,绿意森森,感觉落于眉睫间的光斑都是嫩绿色的。溪水清澈见底。鱼群游过时,投在溪底沙砾上的影子似活了的篆字。石英岩脉过滤出的山泉,如同液态的水晶缓缓流淌。最妙处在于溪床的叠层构造,赭红色砂岩作底,青灰色板岩为架。当枯叶打着旋儿掠过水面时,其倒影竟能清晰映出叶脉的显微结构。
我立于石上,一再惊叹山涧之清澈透彻。这条山涧的源头在龙地自然村,龙地自然村有4亩的风水林,从水尾往下绵延在山涧的两旁。关于这片风水林,龙地黄氏族谱里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护林公约,但自古以来,村民有约定俗成的制约。村民黄永根介绍,他们祖上传下来的规矩,任何人不得进风水林砍伐树木,哪怕只砍下一枝,被人发现了,犯规的人就要杀一头猪请村里人吃,以示赔罪。新中国成立后,犯规的人要请电影队来放一场电影,并向村民检讨。村民说,哪怕是自然掉落的树枝,自然腐朽倒下的大树,他们都没动。百年古木根系织成绵密水网,每场山雨都被涵养成甘泉,终年汩汩渗出岩隙。当现代环保法条还在依赖罚款惩戒时,这方水土早以“耻感文化”构建起比钢索更牢固的生态防线,于是才有了现在清澈见底、从不枯竭的溪水。
龙地溪谷最开阔处在醉仙溪,开阔的河滩原来是村民用来堆放秸秆杂物的,后来白塔、洞口两村打破行政壁垒,联手将烂河滩开发成露营地。可喜的是,他们没有像某些景区进行大开大合的暴力开发,而是以“绣花功夫”对溪谷进行微改造:竹编围栏勾勒田园诗韵,砾石小径串联野趣天地,让原生地貌在最小干预中焕发最大价值。这种开发思维,恰恰是《园冶》所述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的营造智慧。
乱石滩在保留原始肌理的设计中,成就了户外休闲和露营的独特卖点。龙地溪谷消暑有三绝:冷泉漱石、松风筛日、寒潭酿月。循着青灰砾石小径蜿蜒而上,足底棋子般的卵石隔着鞋底传递凉意。山下城镇热浪翻涌时,此处溪风却裹着冷杉树脂的清香,在花岗岩峡谷间酿出天然冰窖。游人将啤酒、可乐浸于浅水处,须臾便得沁骨冰啤和冷饮。老钓客踞坐虎皮石,长竿斜指碧渊。还有自助烧烤、露天电影等休闲项目,不仅能丰富游客体验,还能持续带动周边村民创收,推动生态资源高效转化。这种以生态为基、文化为魂的微改造模式,或许正是破解“千村一面”困局的一个思路——乡村振兴不必推倒重来,有时,只需为沉睡的土地轻轻拂去尘埃。
龙地溪谷有一小屋,应该是小卖部,现在是淡季,所以关着门,要到夏季来临才会重新打开门扉。小屋的外墙上写着“晚风和你,都是我的期待”——当六月蝉鸣撞开溪水的闸门,这被山风摩挲了千百遍的10个字,将会在旅人脚步和笑语里获得圆满。此刻的静默,不过是为重逢预留的留白。(肖爱兰)










